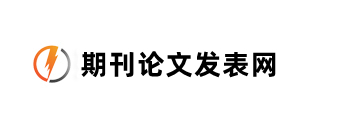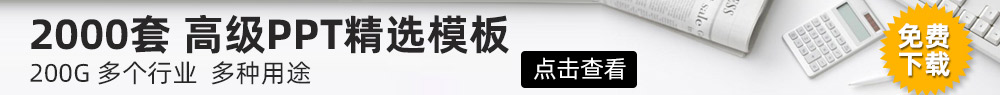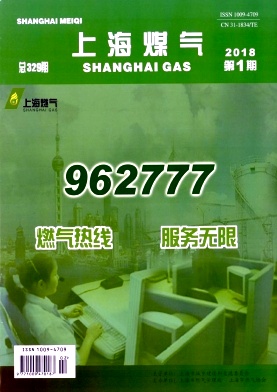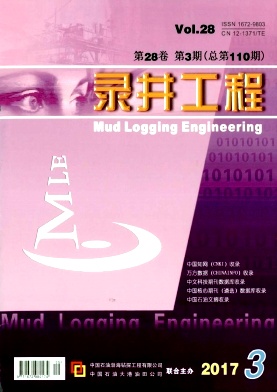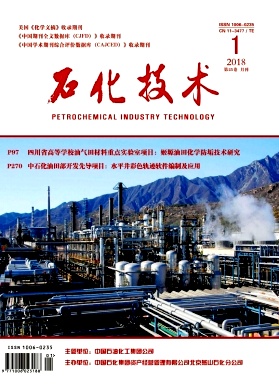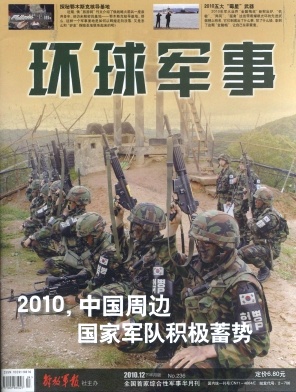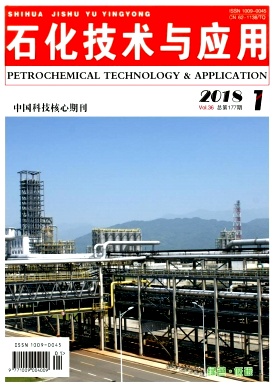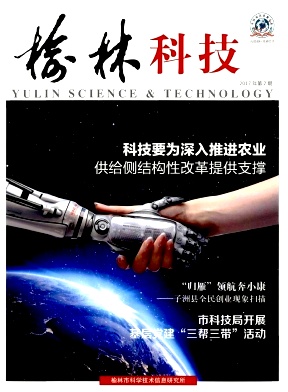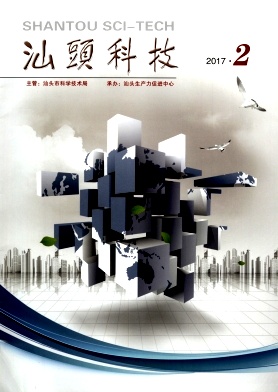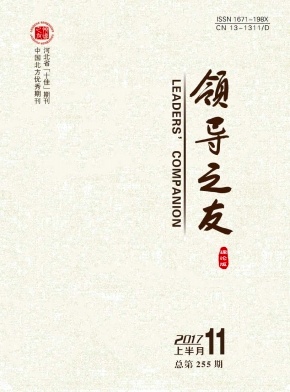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
作者:发表网 如您是作者,请告知我们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简单的理论不应被忽视
儒家人性论一般以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为代表,而性朴论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概念。事实上,儒家性朴论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一理论并不是简单地判断人性是善是恶,而是注重其简单性、原始性、可塑性等。性朴论对儒家教育哲学的影响大于性善论或性恶论。
儒家的性朴理论已经被论者说得很清楚了。周志成认为,荀子本人不是性恶论者,而是性朴论者。《性恶》是荀子后来学到的作品。他在《荀韩人性论与社会历史哲学》(2009年中山大学出版社版)、《荀子是性朴论者,非性恶论者》(2012年《邯郸学院学报》第四期)、《荀子非性恶论者辩论》(2009年广东社会科学第二期)、荀子:性朴论者、非性恶论者(2007年3月20日光明日报)阐述了这一观点。本文同意这一观点,并从性朴论的角度考察儒家教育哲学。
周炽成主要从《荀子》文本内外两个方面来说明荀子是性朴论者,而不是性恶论者。在《荀子》文本中,《荀子》只有一篇文章(《性恶》)主张人性恶,而有大量的文章主张或显示人性朴素。《礼论》说:“性者,原本简单;伪者,文理隆盛。无性,伪之无所加;无伪,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圣人的名字之一,天下之功就是这样。所以说: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随之变化,性伪合而天下治。“一般来说,研究荀子人性论的人都会注意到“性者,原始朴素”这句话,但他们不会认为它与《性恶》的著名观点有冲突,而周炽成则意识到了这种冲突。在他看来,性朴和性恶的区别非常小。“原始朴素”的性绝对不能说是恶。就“无性,伪之无加”而言,朴之性似乎具有符合善的潜力,但从“无伪,性不能自美”的角度来看,朴之性显然不够完美,如果用“恶”来概括这种不完美,肯定不能说过去。周炽成认为,性朴的思想不仅清楚地表达在《礼论》中,还表现在《荀子》一书中的《劝学》中、《正名》、《荣辱》、《儒效》、《大略》等篇。《劝学》一词:“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槃,与之俱黑。王念孙在解释这句话时指出:“这句话善恶无常,唯人所习。[1]蓬本性不直,但如果出生在直麻中,自然会变直;本性是白色的沙子,如果放在黑色矿物中,自然会变黑。性朴论强调性的可变性,这是《劝学》的一个基本观点。《荣辱》一词:“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这也说明了人性的可变性和后天行为、环境的重要性,从而反映了自然的朴素,自然的不恶。儒效也有类似的说法:“居楚而楚,居越越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是,积极也是如此。“大略”的说法更值得注意:“不富不养民情,不教不理民性。家乡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不夺其时,所以富之也。设置大学,设置乡序,修六礼,明七教,所以道之也。诗中说:‘饮食之食,教导之教。王事具就够了。“理民与养民并列,当然意味着性不是恶,不像《性恶》所说的那样需要重生。以教来“理”的性与“礼论”、《劝学》等文章所说的性同样简单,既不能说纯粹的善,也不能说纯粹的恶。理性的本义是加工、雕刻玉石。“说文解字”说:“理,治玉也。“韩非子?”和氏说:“王乃使玉人理其朴而得宝,随后命令说:‘和氏之璧。“玉来自玉,玉含有玉的材料,而一块普通的石头无论如何都不能加工成玉。与此类似,人性中含有好的素材,如果没有这种素材,就无法实现现实中人的善良。然而,就像玉中含有杂质一样,人性并不完美,而“教”可以去除不完美的成分。
除了荀子的文字外,荀子的著名弟子韩非子、李斯都没有断言人性恶,也没有说他们的老师主张人性恶。“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孟子和荀子作传时,并没有提及他们在人性问题上的分歧。如果像后人认为的那样,孟荀最大的分歧就是前者主性善,后者主性恶。那么,既然司马迁把他们结合起来作传,他为什么不在这个传记中提到后人谈论的这个重要分歧呢?[2]虽然司马迁由于篇幅有限,无法一一讲述孟荀的所有思想,但如果他面对后人津津乐道的孟荀善恶争论而不记一句话,似乎也说不出来。更合理的解释是,司马迁没有在《荀子》一书中看到《性恶》或者即使看到这篇文章,也不认为是荀子的作品。此外,西汉的韩婴是荀子后学,他在《韩诗外传》中大量引用荀子,但不引用《性恶》。因此,周炽成大胆推测:“韩婴写《韩诗外传》时,《性恶》很可能还没有出版,或者即使出版,他也不会把它归咎于荀子,所以他没有引用它。西汉时期讨论人性最著名的思想家董仲舒继承了荀子的性朴论。董仲舒说:“性者,天质朴也;好者,王教之化也。如果没有其质,王教就不能化;如果没有其王教,就不能简单善良。[4]这与之前引用的荀子《礼论》中的说法相同。董仲舒以“天质之朴”为人性,而荀子则以“原始材朴”为人性,两者高度一致。董仲舒的性朴论可以证实荀子的性朴论。董仲舒批评孟子的性好理论,认为他把善的标准定得太低,把“善”(善的潜力)作为现成的、完整的善。董仲舒用米与禾、茧与丝、卵与鸡等具体例子来说明善质与善的区别。米等于善,和等于善。米饭来自和,但不能说和即米;善来自善,但不能说善就是善。董仲舒认为,孟子说人性好,就相当于说禾即米、茧即丝、卵即鸡。当然,与《性恶》作者对孟子性善论的激进批评相比,董仲舒的批评是温和的。周炽成将这两种批评联系起来,得出了意想不到的结论:“性恶很可能是西汉后期的作品。有些人可能会看到董仲舒对孟子性理论的批评过于温和和过瘾,所以他用更激烈的话语和更极端的立场来批评它。这个人或这些人就是《性恶》的作者...如果《性恶》确实是荀子写的,那么对人性善恶问题有着深刻关注和荀子深厚渊源的董仲舒肯定会读过;如果董仲舒读过这部批评孟子性善论的作品,也批评过这篇作品,他不提性恶论,这是很难理解的。如果你是董仲舒,你知道以前有人从性恶论的角度批评过性善论,但你必须从另一个角度批评它。你不能面对性恶论吗?如果性恶论成立,你温和的批评有什么意义?如果性恶论不成立,你为什么不提这个理论呢?因此,合理的推断是:在董仲舒之前,《性恶》还没有出现。董仲舒没有读过《性恶》与司马迁、韩婴没有读过它可以互相支持。三人生活的时代非常接近,他们都是西汉中期的人。简而言之,有一个连接的证据,形成了一个证据链,表明《性恶》不太可能在西汉中期之前出现。”